鐘會為什麼選擇叛變?真相是什麼
今天小編給大傢準備瞭再世張良的鐘會為什麼在匆忙之間會叛變呢?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三國時期的鐘會出生在一個政治傢庭,他的父親是曹魏時期著名的政治傢和書法傢鐘繇,鐘繇在曹丕時期與王朗、華歆並稱三公。
鐘會出生的時候,鐘繇已經是75歲的高齡瞭,鐘繇老年得子,自然對這個兒子十分喜愛,對他這個兒子的生母張昌蒲更是寵幸得不得瞭,但張昌蒲身份隻是個小妾,鐘繇使出瞭渾身解數,休掉瞭原配,在死之前將鐘會的生母張昌蒲扶正。
因為她母親的身份,他媽媽沒少受到傢裡人的欺負。鐘會出生沒幾年,他的父親就去世瞭。鐘會與他母親隻能相依為命,他的母親教會他讀書識字,並撫養他長大成人。

對此,長大後的鐘會對他的母親感情特別深,在她母親去世後,他為此專門寫瞭一篇關於他母親的傳記來回憶母親的學識和教他做人的道理。並不顧當時世俗的反對,以正室的身份將母親下葬。
小時候的鐘會,特別地聰明,學東西非常快,又讀瞭很多書,並很快小有成就,名聲遠揚。
年輕時候的鐘會十分要強,性格倔強,也不服氣誰。後來有一次,他去拜訪當時的名士嵇康,嵇康正巧與友人在門前的大樹下煉鐵,頭也不抬也不招待鐘會,鐘會站瞭好一會兒,自感無趣,就悻悻離去。
他準備走的時候,嵇康突然揶揄地問瞭他一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憤憤地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雖然鐘會沒有說什麼,但還是覺得嵇康瞧不起自己,覺得自己受到瞭羞辱。這也為後來促使司馬昭殺掉嵇康埋下瞭伏筆。
除瞭讀書,鐘會還經常與司馬師、司馬昭兄弟、陳騫、陳泰等高官子孫們一起玩耍,應該說鐘會與司馬氏兄弟從小知根知底,互相還特別的瞭解。可能在那個時候,鐘會尚未把司馬兄弟當成自己的主子。
但高平陵的事變改變瞭鐘會的一生,他也徹底地看清瞭形勢,主動投靠司馬師兄弟,這在當時也是很現實的選擇。相比起夏侯玄等人來說,鐘會並不是一個忠臣,他也沒有沒想過去當一個忠臣,而是見利而動,艱難地把從一朝兒時的玩伴突然變成君臣關系。
司馬師在完成平叛毌丘儉之後,回師途中病逝於許昌,按當時魏帝的詔令是讓傅嘏帶領軍隊先行回朝,讓司馬昭留鎮許昌,但政治上極為敏感的鐘會看出這是個政治幌子,因為他深知魏帝曹髦絕不甘心當一個傀儡皇帝,他曾提醒過司馬師說這個皇帝“才同陳思,武類太祖”。
鐘會這時作為司馬昭的腹心之臣,開始與傅嘏積極謀劃應對,一邊寫信說明情況,一邊簇擁著司馬昭率領著大隊人馬往回趕,並在洛陽郊區紮下營盤,察看朝廷動靜,魏帝曹髦果然泄氣,見到大軍壓境,無奈之下隻得下詔封司馬昭為大將軍,接管兵權,並統理朝政。

正因為有著鐘會這次的極大幫助,司馬昭才安穩地接管瞭司馬師的權力,因為這件事,鐘會非常的得意,覺得自己特別瞭不起,自己要是追求起功名利祿來會特別的簡單,便有些飄飄然瞭。
後又隨著司馬昭平叛諸葛誕,鐘會更是一刻不離的為司馬昭出謀劃策,出力很多。這個時候,很多人就誇他是張良在世,計劃的事從來都是言無不中。
鐘會頓時聲名大振,上至皇帝,下至群臣,交口陳贊。從此時起,鐘會更是志得意滿,逐漸對功名心越來越看重。
盡管司馬昭對他非常地賞識,但肯定也察覺到瞭鐘會性格的細微變化,雖然讓他參與處理瞭很多朝廷的機密大事,但兩個人在這時定是有瞭心理隔閡。
聰敏的鐘會為瞭掩蓋自己對權力的野心,一再高調地推脫司馬昭賞給他的高官厚祿,想必他這麼做不僅是讓司馬昭放心,同樣也在等待一個機會。
隨著曹魏外臣如王凌、毌丘儉,諸葛誕等相繼叛亂而亡,夏侯玄、鄧颺、李豐等曹魏內臣被剪除幹凈,司馬昭的野心在這時可謂昭然若揭,鐘會作為司馬昭的心腹,自然心如明鏡,做事也變得小心低調多瞭。
直到魏帝曹髦被司馬昭殺害後,司馬昭一時成為朝廷上下議論的焦點所在,臣弒君,臣還安然無恙,總會惹來很大的爭議。
弒帝的最大推手賈充開始越來越受到司馬昭的賞識,替代瞭鐘會成為司馬昭更重要的心腹智囊。
為瞭擺脫社會的輿論,轉移國內的政治矛盾,也為瞭積累篡位的政治資本,司馬昭就將眼光放在弱小的蜀漢國身上。他知道,蜀漢自從經過諸葛亮、薑維多次出兵,實力更加弱小,已經風雨飄搖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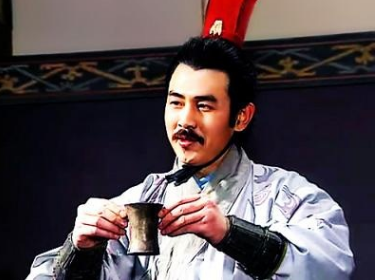
他找來鐘會商量討伐蜀漢的事情,鐘會當然知道司馬昭的初心並不是真的一口吃掉蜀漢,而是為瞭謀取篡位的資本,獲得更大的功績來平抑國內的輿論。
十分聰明的鐘會,主動請纓,接過伐蜀的重任。他覺得,伐蜀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就算不能一舉拿下,也是獲取功名的好機會,這恰恰也是他苦苦等待的最後機會。
在這之前,很多人就早已看穿瞭鐘會的心思,如司馬昭的夫人王氏就曾對司馬昭說:“鐘會見利忘義,喜歡制造事端,如果太抬舉他,給他權力,他一定會作亂,不能給他很大的權力。”
邵悌也對司馬昭說,今天派遣鐘會帶領10萬大軍去伐蜀,隻有他一個人恐怕有點不放心,不如再派其他的人一起去。
知弟莫若兄,雖然鐘會的功名、才智都遠高於他的哥哥鐘毓,但鐘毓曾對司馬昭就說,我弟弟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來獲取功名,但是很難收斂,不能讓他擁有專斷的權力。
可想而知,久在政治權利爭鬥中心的司馬昭對授人以柄這點常識還是非常在意的,雖然他同意給鐘會兵權去伐蜀,但從此時起,他和鐘會的關系也遠不如以前那樣親密瞭,開始對鐘會有瞭戒備的心裡。
不僅給鐘會派遣瞭一個監軍衛瓘,還分兵三路,當鐘會攻入蜀地後,又派遣自己心腹賈充西據漢中察看形勢。
在鐘會和鄧艾取得節節勝利的同時,司馬昭趕忙讓皇帝給自己加官進爵。此時的鐘會猶如蛟龍入海,覺得該是自己建功立業的時候,他為瞭獨掌兵權,誣陷一同進兵的諸葛緒懦弱不會打仗,抓瞭後送給司馬昭處理。
蜀國投降後,又派衛瓘抓瞭鄧艾父子,這時候的鐘會終於掌控瞭二十萬兵馬的大權,開始有瞭非分之想,覺得自己經歷瞭那麼多事,都是算無遺策,論聰明才智,誰能比得上我?論對國傢的重要貢獻,又有誰能比得上我?
他又深知司馬昭防備心太重,如今自己立瞭大功,功高蓋主,司馬昭難保不會對付他,再一想伐蜀這麼隨隨便便就成功瞭,就算攻取天下也不是什麼難事。開始志得意滿,也不把司馬昭放在眼裡瞭。
他覺得憑他的才能,一樣可以跟司馬昭平起平坐,何必一定要屈居在他人之下呢?加上蜀地險阻,即使與司馬昭爭奪中原失敗瞭,也完全可以跟劉備一樣在蜀地稱王稱霸。

司馬昭雖然遠在洛陽,但對鐘會的所作所為從一開始就十分懷疑,等到聽說鄧艾謀反的事以後,就立馬趕到瞭長安,等待事情的變化。
為此,他還專門給鐘會寫瞭一封信,信中說:“我害怕鄧艾不服從朝廷的詔書,已經派遣中護軍賈充帶領著步騎一萬多人進入斜谷,屯守在樂城,我自己帶領瞭10萬的兵馬在長安,說不定我們馬上會再見面瞭。”
這是司馬昭赤裸裸地威脅,意思是讓鐘會別做傻事。鐘會看瞭書信後,不願服輸的他心裡十分反感,他知道就算不謀反這樣回去,也可能被人告發有謀反罪,害怕落個造反被殺的鐘會,知道即使自己想不謀反也不成瞭,倉促之間,起兵造反,最終因準備不足而失敗,自己也落瞭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鐘會、鄧艾一死,司馬昭安心的多瞭,再也沒有很有能力的反對者瞭。而他可以獨占伐蜀的大功,讓魏帝晉封自己為晉王,開始瞭司馬師傢族全面統治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