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晚年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百姓的生活如何
西漢初期,經過高祖、惠帝、呂後、文帝、景帝各代以黃老之學為指導的統治,在近七十年間,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勞動人民創造瞭大量的財富,國傢己擁有雄厚的財力和物力。同時,由於西熾王朝采取削潘政策,在平定七國之亂後,地方諸侯王的實力大為削弱,中央政權日益鞏固,逐漸形成瞭封建大一統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反其先輩的妥協態度,采取積極有為的政策,“外事囚夷,內興功利”,急功進取。這樣,原來那種“無為”的黃老之學,勢必不能再繼續推行瞭,而以維護封建大一統和專制皇權的董仲舒新儒學便應運而生,以這種新儒學為基礎,儒法合流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形成瞭。

漢武帝在策問賢良的“三制”中,明確提出如何效法三王五帝“改制作樂”的問題,以及怎樣解決“天人相與之際”、修德輕刑的問題。董仲舒揣摩武帝的意圖,於是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著述中,以儒傢思想為主,並吸收陰陽五行傢、法傢以及殷周的天命神權等各種有利於維護封建鼓治的思想因素創立一種新儒學。在法律思想方面,他主張“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後來成為指導封建立法、司法的根本原則:他所主張的“德主刑輔”、“禮法融合”,則被奉為統治人民的基本方法。

董仲舒並對“三綱”和“德主刑輔”、“禮法融合”作瞭神秘主義前解釋,力圖說明它們都符合“天意”,並把它們絕對化、永恒化。漢武帝“罷黠百傢,獨尊儒術”,使儒傢思想在法律領域也占據重要地位,這就棒志著以董仲舒新儒學為基礎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已經形成。這種新的政治法律理論,完全適應瞭地主階級加強專制皇權和統治人民的政治需要,自章為他們“長治久安”,鞏固封建統治的思想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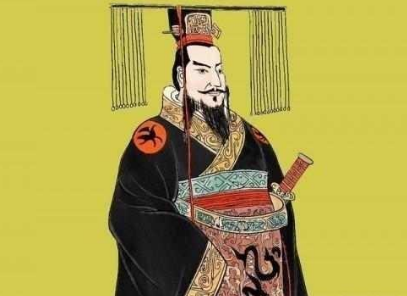
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結束瞭東晉以來近三百年的分裂、濡亂局面,重新建立起多民族的繞一的封建國傢。隋王朝的開創者楊堅為鞏固統一,實行瞭一些改革。他制定和頒行的《開皇律》,體現瞭“以輕代重,化死為生”的原則,對後來中國封建法制和法律思想的發展產生瞭重要影響。

唐太宗鑒於隋朝驟亡的教訓和農民革命的威力,執政伊始即以“崇儒”為基本國策。唐太宗聲稱“聯今所好者,唯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還常拿先秦儒傢“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來教訓太子。貞觀初,曾對待臣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他置弘文館,封孔子為“先聖”,顏調為“先師”,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造成“儒學之興,古昔未之有也”的景象。這方面的思想從積極面來看,有利於社會安定,促使他確立“安人寧國”的治國方針。在政治法律觀上,太宗主張:“德主荊輔”,強調德刑結合,重在教化,在他看來,德刑是統一的,禮法應當酷合。魏征勸諫太宗:“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

太宗說:“聯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泊者,國祥延長,任法禦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亡亦促。”在立法和執法上力求“惟須簡約”,“慎獄恤刑”“禮法迭相為用”,長孫無忌主修《唐律疏議》中明確規定:“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正道出瞭唐代法治指導思想的真諦。這些原則成瞭政治傢、思想傢思考法律問題的模式。這標志著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已經成熟,禮法結合基本定局。隋末楊氏王朝的殘暴統治和無休止的征調榨取,造成“傢傢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床,”出現瞭“萬戶則城廓空虛,千裡則煙火斷滅”的悲慘景象。但在唐代,唐太宗所主持的唐初法制建設中,倍加重視有關經濟方面的立法。從貞觀到開元,社會生產力都得到迅速發展,經濟繁榮,文化燦爛,國力強盛,成瞭當時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傢。這種局面的產生,是與唐太宗等唐初統治者運用法律手段保護和促進封建經濟的發展分不開的。

唐朝建立以後,為瞭恢復殘破的經濟,滿足征收賦稅和兵役的需要,繼續推行均田制。《舊唐書·食貨志》說,武德七年(624)頒佈“均田令”,規定:男丁十八歲以上給田一頃,其中十分之二為“永業田”,十分之八為“口分田。”老男、殘廢人給四十畝。寡妻妾給30畝,8日自立戶頭增加20畝。“永業田”歸私人所有,可以繼承和在一定條件下買賣。“口分田”則歸國傢所有,身死後由官府收回,另行分配。這些規定是為瞭利用小土地私有制的形式。施惠於民,“其目的不是給農民保證生活資料,而是給地主(保證)勞動人子”,是為瞭掩蓋封建的特權法律下的超經濟剝削。

為保障“均回令”的實施,在唐太宗所修訂的《貞觀律》中規定瞭“占田過限”、“妄認盜賣公私田”、“盜賣或盜種公私田”、“賣口分田”、“裡正授田課農桑違法”等罪,分別明確地規定瞭答、杖、徒刑等不同的處罰,使“均田令”被有效地付諸施行。這不僅有利於增加國傢的財政收入,同時也保護瞭自耕農的利益,有利於唐初農業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為唐代盛世的來臨奠定瞭經濟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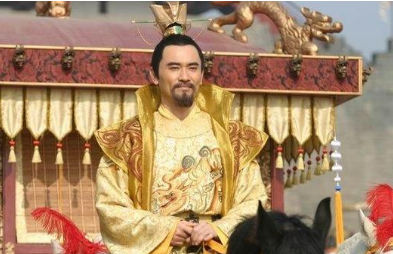
唐初財政立法主要是“租庸調法”,是與均田制相配套的一項財政法律制度。這一制度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將地租和德役合一,使封建官吏和整個地主階級得到德役地租和實物地租的雙重封建剝削。“租庸調法”規定:租,是對國傢所授田地應交的回賦,每丁每年納粟二石或稻三石:調是按戶征收。隨鄉土所產,蠶鄉每丁每年納緩、絹、各二丈,綿三兩,非蠶鄉納佈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是人丁對國傢應服的勞役,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閏年加二日,如不服役,每日納庸絹三尺或佈三尺七寸五分。還規定:“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為瞭保證它的實施,《唐律·戶婚》的《差科賦役違法》和《輸課稅物違期》等條,規定瞭從答四十直到死刑的嚴厲懲罰。唐初推行的租庸調法,保證瞭封建國傢的賊稅和德役,從而保障封建國傢機器的正常運轉。這對以後的賦稅制度產生深遠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