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之圍:蕭繹將南梁從ICU推進瞭太平間!
江陵之圍:蕭繹將南梁從ICU推進瞭太平間!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傢參考。
如果你來到公元554年十月的江陵城,你一定會看見一個令你瞠目結舌的現象:
城外煙塵滾滾,大批西魏士兵正在源源不斷地向江陵挺進,準備對這座南梁的新都城發動進攻;城內也早已下達瞭戒嚴令,這個冬天充滿瞭肅殺。

皇帝蕭繹的宮中,自皇帝以下所有的百官都換上瞭軍服,面容嚴肅的聚在一起。然而,他們並不是在商議破敵之策,而是在聽皇帝的經筵日講。
之前下達戒嚴令的時候,蕭繹也專門停掉瞭這個講座;而當一封宣稱未見魏兵的偵查奏報遞到禦前的時候,蕭繹便又重新開始瞭他的文化課學習,還要求大傢和他一起學。兩道命令之間的時間間隔,連24小時都沒有。

(配圖為明朝經筵日講)
在侯景之亂被平定以後,蕭繹頓時成為瞭南朝的國傢英雄(雖然他的弟弟不買賬)。而在大亂平定以後,蕭繹下的一道手諭卻耐人尋味——他讓前敵總司令王僧辯把在建康的幾個侄子全殺瞭。
半年以後,除瞭那個不識相的蕭紀以外,已經沒有人可以再威脅到蕭繹的地位。於是蕭繹就在三請三讓的戲演足瞭以後,正式在江陵登基稱帝,史稱梁元帝。

奇怪的是,蕭繹卻並沒有前往建康登基,反而一直呆在江陵。至於原因,官方給出的說法當然是因為侯景之亂使得江東民生凋敝,不忍再靡費民力之類的話。實際上的原因,卻可以總結成兩點:
一,江東一帶一塌糊塗不假,但是有很多鍋不能賴在侯景頭上,蕭繹派去的官軍甚至比侯景部還狠,這個我們以後還要再講;
二,蕭繹的部下基本都是楚地的人,不願意去下遊當客人,就待在中遊就蠻好。

在這兩種因素的合力之下,蕭繹就在江陵踏踏實實地當起瞭他的皇帝。
五十多年前,南齊的最後一個皇帝蕭寶融,也是在這裡當的皇帝;不久以後,他就死瞭。
熟讀經史的蕭繹,不會不知道當年的故事;然而,在別人勸說他的時候,他卻丟出瞭一句相當硬氣的話:“吉兇在我,運數由天,避之何益?”

記住這句話,因為很快蕭繹就會自己打自己的臉。
蕭繹登基的時候,各地呈上來的不是祥瑞,而是各種各樣的災異,甚至連淮南都出現瞭野象踐踏農田的異聞。這一切仿佛都在預示著,這個茍活於江陵的政權的年壽不永。

果然,在吃掉益州以後,西魏展現出瞭更多的領土訴求。他們先是讓楊忠發動南侵,實現瞭以安陸為界的劃地而治;又在不久以後發動瞭以柱國於謹為統帥的旨在滅亡南梁的戰爭。
南征以前,有人問於謹,蕭繹會如何應對這一次進攻?於謹開出瞭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抓緊時間遷都建康避其鋒芒;中策是命令百姓堅壁清野等待援兵;下策則是一動不動等著挨打。而且於謹還很有把握地表示,蕭繹一定會采取下策,也就是沒有對策。

遠在江陵的蕭繹應該是沒聽到這段對話,但是他用腳投瞭於謹的贊成票。
魏兵發兵第二天,急報就送到瞭江陵,蕭繹也召開瞭禦前會議。然而會開出來的結果,卻是這樣一句話:
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

好不容易有個人自告奮勇地去偵查一下,結果轉瞭一圈沒看見魏兵,就心安理得地告訴皇帝,那些說西魏來打咱們的是假情報,您安心燒高香吧。
蕭繹雖然糊塗,但也沒全信。但是他所做的安排並不是加緊戰備或者商議遷都,而是讓大傢穿著軍裝去聽他的經筵日講。
在滿城戒嚴之下,一群穿著軍服的文官和一群半懂不懂的武官,坐在一起,聽著皇帝親自登臺講授《道德經》。這個畫面,在黑雲壓城城欲摧之下,多瞭幾多滑稽。

更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是,蕭繹拒絕瞭周邊部隊的勤王請求,卻要求遠在建康的王僧辯帶兵逆流而上。當別人問道為何如此時,正在夜觀星象的蕭繹隻悲傷地回瞭一句:
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
一個月後,魏軍先頭部隊抵達江陵城下,被梁軍擊敗。然而短暫的勝利卻並沒有能轉換成戰略上的成功,在西魏大部隊團團將江陵包圍以後,城內城外都不在懷疑,陷落隻是時間的問題。

手下向蕭繹提出魚死網破、決一死戰,蕭繹拒絕瞭;他們要求斬殺幾個皇帝身邊的佞臣,又被拒絕瞭;最後,幾個大臣苦苦勸告皇帝化妝逃出城,還是被拒絕瞭。江陵之圍,就在蕭繹近乎認命的狀態下宣告城破。
當魏兵攻入江陵內城的時候,蕭繹沒有組織抵抗,也沒有正襟危坐等待敵人到來,而是跑到藏書閣,把他所藏的十四萬卷圖書付之一炬。事後,當西魏仆射長孫儉問道此事時,呆若木雞的蕭繹隻回答瞭十一個字:“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此時昭明太子蕭統的兒子蕭詧已經投靠瞭西魏,封為梁王,並被定為下一任傀儡政權的皇帝。而於謹很不厚道地把蕭繹發配給瞭蕭詧處理。這位侄子在百般凌辱瞭自己的叔父以後,又極力主張處死蕭繹及其子嗣,並在蕭繹死後,“厚葬”瞭他:
使以佈帕纏屍,斂以蒲席,束以白茅,葬於津陽門外。
蕭繹的這條命,就算是這麼交代瞭。對於這個人,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評價。

應該說,把南梁折騰的奄奄一息的,是昏聵的蕭衍和殘暴的侯景;而把南梁從ICU推到太平間的,就是他蕭繹瞭。
在侯景肆虐的時候,蕭繹等人沒有同仇敵愾共同對敵,反而自己內鬥的一團糟,甚至不惜請外國來幫助自己滅掉自傢兄弟。無怪乎《南史》的作者都要悲憤地寫道:
自侯景之難,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爲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南,復爲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裡而近,人戶著籍,不盈三萬。中興之盛,盡於是矣!
如果說司馬睿的“元帝”之謚好歹還是有割據江東的實際功勞的話,那麼蕭繹的“元帝”純粹就是後人的貼金瞭,這個送給中興之主的謚號放在他身上幾乎就是諷刺。

甚至就連蕭繹的敗亡,都給後人留下瞭巨大的災難。他的焚書,被認為是焚書坑儒以後中國文化史上的又一次浩劫。他一人之死雖不足惜,然而他的死卻連累著整個荊州的百姓跟著他一起受苦,就顯得太混賬瞭:
於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大玉徑四尺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馀傢,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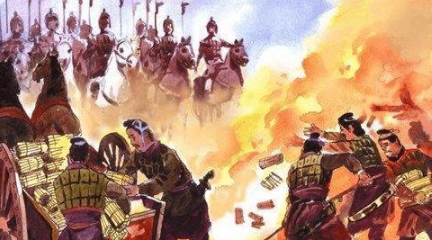
這支西魏的部隊裡,上到高級統帥楊忠,下到最底層的官兵,都多得是漢族人。而這些人在面對自己的同族骨肉的時候,似乎下手並不比當年的五胡十六國更輕。底層士兵尚且不論,作為副帥的楊忠自始至終不發一言,實在是很耐人尋味的事。
直到蕭繹死,他心心念念的王僧辯也沒能來到江陵。那麼,這位平定侯景的第一功臣又去瞭哪兒呢?他最後的歸宿又是怎樣的呢?咱們下回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