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田賦制度是怎麼樣的?“租庸調”是怎麼來的?
今天小編就給大傢帶來唐朝的田賦制度是怎麼樣的?希望能對大傢有所幫助。
作為一個喜歡歷史的人,除瞭看那些文治武功、內政外交之外,其實最關心的就是這個國傢對自己的老百姓好不好瞭。除瞭天下大亂時期,人民的生活更多是取決於什麼呢?那麼無疑就是這個朝代的賦稅制度瞭。所以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瞭解一下唐朝時期的賦稅制度,看看唐朝時期的農民一年要繳納多少稅。

租庸調制:富人可以很富,但窮人不能太窮
中學歷史課上,我們學過,唐朝的田賦制度,叫“租庸調”。
何為租?
假設你性別男,出生在初唐,那麼,當你18歲成年時,國傢會分給你100畝田地。
這100畝田地中,有20畝叫永業田,可以傳給子孫,相當於你傢的私產瞭;另外80畝,叫口分田,六十歲後,要還給國傢,相當於租給你種,但你要交稅。
交多少稅呢?每丁每年向國傢交納粟二石,換算成現在的計量單位,大約是200斤谷子。
這個稅負,可以說是非常輕瞭。收入繳納比例,是四十稅一,也就是說,收成40斤,交1斤稅。漢代是三十稅一,相比已經減輕不少。
這種國傢配給農民的田地,就叫“租”。
各位可以在心裡默算下,如果你有100畝地是什麼概念?嗯,妥妥的小地主。
雖然80畝要還給國傢,但20畝永業田,三代下來,你傢也有60畝私產瞭。
但註意,你傢的永業田,是不能隨意買賣的。除非是遇到特殊情況:民戶有身死,傢貧無以供葬者,可聽賣永業田。
這看似不自由,其實是個好事。不能私賣土地,一來可以防止土地兼並,二來,可以防止那些“崽賣爺田不心疼”的敗傢子敗光傢產。
為何在初唐時期,有這麼多田地分給人民呢?
這其實是延續瞭北魏的“均田制”。北魏時期,北方戰亂連連,人民流離失所,導致田地大量荒蕪,國傢稅賦也隨之減少,入不敷出。為瞭改變這種現狀,北魏政府控制的田地,分給農民,農民向國傢繳納租稅,並承擔一定的兵役和徭役。
唐朝開國時,情況類似。
經過隋末戰亂,到李唐統一全國時,民生凋敝,人口不足300萬戶,比隋朝巔峰時期的900萬戶,減少瞭三分之二。
人口急劇減少,田地大量荒蕪,所以唐朝延續瞭“均田制”,將土地分給人民,輕徭薄賦,使得生產快速恢復,國力迅速得到瞭提升。

何為庸?
庸,就是徭役,是人民對國傢的義務勞役。
一個國傢,總會有很多公共工程,大到修長城這種國防設施,小到修路修渠,當然,還有皇傢宮殿、官衙等。
那時候沒有專職的工人,就得靠人民服役。這在歷朝歷代都一樣。
那麼,如果你是唐朝的一個農民,你一年要服役多少天呢?不多,二十天,如果碰到閏月的年份,則加兩天。相比漢朝的三十天,大大減輕瞭你的負擔。
如果國傢這一年工程比較少,不需要你服役呢?那你需要每天交納絹三尺,或佈三尺七寸五分,交足二十天即可。這在歷史上有個名詞,叫“輸庸代役”。
相反,如果今年政府工程很多,二十天義務勞役外,還需要你多服役呢?放心,不會讓你吃虧,加役二十五天,那你們傢的“調”(佈匹)就不用交瞭;加役三十天,那你傢的地租和佈匹都免瞭。
政府規定,每年的額外勞役,不得超過三十天。

何為調?
在古代的農業社會,描述一個幸福的傢庭,我們常用一句話形容:男耕女織,桑麻滿圃。
傢裡的男人下地耕種,女人則在傢養蠶織佈。
男人種田交地租,那麼,咱們女同胞是不是也要為國傢做點貢獻呢?
要的,那就是把佈絹貢獻點給國傢。
每個傢庭,要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佈二丈五尺、麻三斤,這就叫“調”。

漢唐賦稅制度比較
介紹瞭租庸調,我們簡單將漢代和唐代的賦稅制度比較一下。
在漢代文景之治時,也是輕徭薄賦的典型,漢文帝甚至創造瞭個歷史:前167年,他曾頒佈“除田之租稅”的詔令,免除全國地租。
但漢朝田地是可以自由買賣的,如此一來,到後期時,土地兼並越來越嚴重。勛貴豪紳莊園萬畝,貧民卻為立錐之地,隻能租地主的地耕種。地主收佃農的租,高達十分之五,但卻隻用向國傢繳納三十分之一。
如此一來,富瞭地主,苦瞭貧農。
除瞭田地外,鹽鐵等生意,由民間商人自營。
但到瞭漢武帝,國傢頻繁對外征戰,軍費激增,國庫入不敷出。怎麼辦?漢武帝想到瞭一個辦法:讓商人捐錢。
到瞭自己包裡的錢,再拿出來比較難,商人捐錢不積極。
這下漢武帝不幹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林河海都是朕的,我允許你們煮海為鹽,開山煉鐵,現在國傢有需要,你卻不想做貢獻?
那好吧,以後自然資源都收歸國有,私有企業都關瞭,將鹽鐵改為國營,收入歸國庫。
這種“鹽鐵政策”,為民有經濟戴上瞭一個緊箍咒,不讓民間太富。
但另一面,因為土地大量兼並,底層人民卻很窮。
相比之下,唐朝的租庸調制,使人民“耕者有其田”。有丁就有田,有丁有田就有傢,老婆孩子熱炕頭,挺好。
而商業上,唐初並不限制,商人比較自由,而且不用交稅。當然瞭,代價就是地位很低,士農工商,排在最後。
這樣一來,唐朝富人可以很富,但窮人不會讓你太窮。
不過我要強調一句:這種人民的理想生活,隻局限於初唐。
為啥?往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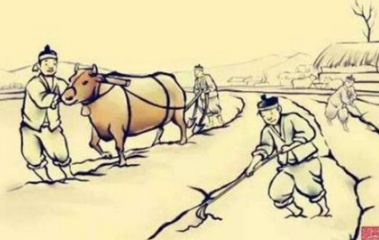
租庸調的瓦解
任何好的制度,隨著社會發展,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租庸調也不例外。
首先,土地不夠分瞭
唐初土地分配政策,有一個巨大的Bug。
在初期時,因為人口少,土地多,政府有足夠的土地分配給農民。
可是,隨著國傢一統,休養生息,人口會越來越多,而且成為私有的永業田也代代累積,如此一來,可分配的地少瞭。
貞觀年間,唐朝人口還隻有300萬戶左右,到瞭武則天神龍元年,漲瞭一倍,達到瞭615萬戶。發展到玄宗天寶年間,人口達到巔峰,達到瞭900多萬戶。
人口漲瞭三倍,土地卻隻能那麼多,如此一來,新增人口就不能保證分到100畝地。
但不合理的是,租庸調是按定額收取的。
也就是說,雖然你傢的地變少瞭,但攤派到你頭上的稅,並沒有變少。
這誰受得瞭。
發展到矛盾最激烈的時候,一些底層貧民隻能逃亡,以避免稅負。

其次,不用交稅的特權人群開始兼並土地
每個朝代,都存在著一些“不用交稅”的特權人群。
唐朝人分為兩種,“課戶”和“免課戶”。
課戶就是普通老百姓,很抱歉,你種國傢地,就得當差納糧。
免課戶呢,嗯,擁有大片土地。比如,你是有爵位的貴族,或者五品以上官員,可以分到五頃到一百頃的永業田;你是有軍功的軍人,根據級別,可以分到六十畝至三十頃的永業田。關鍵是,你不用交稅。
除瞭貴族、官員不用交稅,還有個大傢容易忽視的——寺院僧尼也不用交稅。
如此一來,產生兩個問題:
一些課戶想方設法取得功名,有瞭一官半職,或者幹脆出傢,就成瞭免課戶;
另外,雖然土地不能隨意買賣,但一些底層老百姓實在混不下去瞭,迫於無奈,於是私自將田產轉讓給免課戶,政府也很難管得過來。
於是,土地兼並,這一歷史性太難題,還是在唐朝出現瞭。

最後,租庸調的大難題:賬籍統計
租庸調之所以能順利實施,靠的是嚴密的賬籍。
該收你傢多少租,多少調,依據是戶籍;戶籍之外,還有一本“賬”,統計的是壯丁男子,按這個賬本記錄,來派“庸”,也就是徭役。
唐代的規定是,一年造一次賬,三年造一次籍。
賬籍分三份,一份存縣裡,一份送州,一份呈交戶部。
這個活,不輕松。
國傢這麼大,經常要調查、登記、改動、校對,非常麻煩。
就算是現代社會,有公路,有車,有電腦,有通訊設備,很多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也是很難的一件事,就這條件,還存在很多黑戶。
那我們想象一下古代,交通基本靠走,沒有摩托車,更沒有小汽車,基層公務人員也很有限;最最關鍵是,記錄基本靠紙,但紙張很貴很貴,沒有那麼多草稿紙給你用。
今年熱播的《長安十二時辰》中,大傢還記得徐賓造紙那個情節嗎?
徐賓賣瞭自己的永業田,就為瞭造出更先進的紙,因為原來的紙供應不上政府文書所需瞭。他認為這是關系到天下民生的大事。
確實是這樣啊各位,為什麼漢唐時上層階級都被世傢大族壟斷瞭?因為如果你是個貧民子弟,你是讀不瞭書的 —— 哪有紙給你印書啊!
嗯,徐賓是個好同志。
言歸正傳,交通不便,人員不夠,紙張不足,如此艱難的條件下,初期辦事人員還能靠著奉獻精神盡職盡責,不辭辛勞。時間多久,難免出毛病,比如:你們村有老人滿60歲瞭,或者去世瞭,名字沒有及時銷去,80畝口分田也就沒有及時收回再分配;有孩子滿十八歲瞭,可是沒有人來登記,也就沒有及時授田;離村子很遠的地方,有兩戶人傢,登記人員一看,我去,路都沒有,不去瞭……
總之,有太多因素,會造成賬籍的疏漏。
以上三種主要原因,逐漸造成瞭租庸調制的瓦解。
安史之亂爆發,百姓再一次大規模的流離失所,地方大亂,租庸調徹底實行不下去瞭。
於是,唐朝中後期的另一個稅賦制度誕生瞭。

兩稅制
唐德宗時期,宰相楊炎制定瞭一個新的經濟政策:兩稅制。
為瞭避免把大傢繞暈,我整理出幾個重點特征:
一、政府要用多少錢,就向全國攤派多少稅
以前收稅,是按照固定的比例征收。現在變瞭,政府按照前幾年的支出情況,先定個來年預算,然後按照這個預算總額,向各地攤派。
說實話,按照政府本意,是想“量入為出”,防止無限制的剝削老百姓。可現實中一實行,就出問題瞭。
如果是大唐中前期還好,國泰民安,政府要用多少錢,大概不會相差太多。可是到瞭中後期,藩鎮割據,皇權微弱,甚至還有大大小小的起義,那要用多少錢就不好說瞭,一旦財政緊張,免不瞭要加收稅額。再一攤派,反而容易橫征暴斂,百姓遭殃。
所以有人奇怪,中後期的皇帝,也有幾位猛人,為什麼收拾不瞭那些不聽指揮的節度使呢?一大原因就是,沒錢,打不起仗。

二、戶籍自由流動,有多少地,交多少稅
關於這一點,官方的說法是:戶無主客,以見居為薄。
啥意思呢?簡單說就是,你是陜西人,搬傢到四川去,那你就在四川當地落戶,加入四川籍,不分主客。
嗯,這倒是挺好,畢竟現在你想把戶口遷到其他地方去,也是很難的。在唐代兩稅制時,你就可以自由遷徙瞭。
但壞處是,那些土地肥沃寬廣的地區,人口越來越多,賦稅攤下來,每傢反而很少。
那些貧瘠的地區,村裡可能已經有一半人遷走瞭,可是地方的稅額還是那麼多,一攤派,五傢人要承擔十傢人的稅。
這誰頂得住啊?頂不住,於是剩下五傢人可能也要被逼逃亡瞭。
兩稅制又說: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
在之前,你傢交多少稅,是固定的,不管你傢有多少地,傢境是富有還是貧窮。
現在不同瞭,你有多少地,就按比例收你多少稅。
但另一方面,政府也不再給你分土地瞭,田地又開始自由兼並。是地主還是貧農,看你自己本事。
結果又回到瞭漢代老路,土地兼並越來越嚴重,而且達官貴人還會想方設法瞞報自己的田產,從而少交稅。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清朝。耕者不能有其田,任由地主來盤剝。
忍不住一聲長嘆:苦的總是老百姓。

三、租庸調合並成一項,一年分兩次征收
上面我們分析瞭,租庸調要靠嚴密的賬籍統計,而且分成三項,實施起來難免麻煩。
兩稅制上來,直接將三項合並瞭,直接收錢,分夏秋兩次征收(所以叫兩稅制)。
沒錯,不收你的糧食瞭,也不收你的佈絹瞭,都換算成錢來交。
嗯,政府省事瞭,滿意瞭。
但百姓不滿意。
以前我交200斤谷子就好瞭,現在你要我交500塊錢,我不但要把谷子背到集市去賣,關鍵是,還要被奸商們坑害。本來一斤谷子兩塊錢,但現在收購商勾結起來,隻給我一塊。
我太難瞭,但沒辦法,隻能賤賣,然後把錢交給國傢。
這還不是兩稅制最大的毛病,最大的毛病是,本來租庸調合成一項征收瞭,按理說,國傢再需要服役時,就應該政府出錢去雇人。可是搞著搞著,政府又忘記瞭,有徭役時,仍然讓人民去服役。
真是豈有此理。
到瞭宋代,王安石變法,又要征收免役稅,這其實就是在變相重復征收瞭。司馬光老先生反對變法,理由就是:社會財富是一定的,國傢多收,人民就窮;國傢少收,人民就富。
要國富還是民富,這就要看統治者的良心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