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分析明朝滅亡之根本!東林黨、崇禎都不是主要因素!
今天小編為大傢帶來客觀分析明朝滅亡之根本!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南明為什麼沒抗住?地盤也不小,民心也沒丟多少。東林黨占主導地位,閹黨很多不是投敵就是回傢種地瞭,按說此事該治國瞭吧?他們幹瞭什麼?武將軍閥化不聽朝廷號令是一方面,東林黨文官就起好作用瞭?東林黨有好人不假,鳳毛麟角,改變不瞭印象。要真想做出點啥來,重新統一難,劃江而治總不難吧!
第一,一個王朝活瞭近300年已經是很長瞭,王朝末期各種問題積重難返,社會階層到瞭重新洗牌的時候,不是一個黨派,一個人的能力就能扭轉乾坤的。縱觀歷代王朝哪一個能在300年大限到來之際起死回生的?兩漢交替劉秀雖是漢朝後裔但實際上整個統治階層都已經重新洗牌瞭,西漢原來的貴族豪強被東漢另一批新興貴族取代。

第二,武將軍閥化的確東林黨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比如高傑身死,其妻欲讓高傑之子拜史可法為義父,史可法本該抓住機會控制高傑部隊,卻因為嫌棄高傑的流寇身份沒有接受。可以說整個南明就亡於這種內部爭鬥,不夠團結之中。但內鬥的鍋不應該全推給東林黨,鄭氏集團,流寇集團,順案逆案參與人員都在內鬥,實在是沒有辦法之事。東林黨也無法置身事外,但至少,張慎言,史可法,劉宗周為國之心也是真的,他們以身許國便是明證。孫可望,鄭成功都有私心,雖然功勞上他們更大,但最終他們的私心也導致瞭南明覆滅。
第三:劃江而治,沒有強力的反擊,劃江而治隻是空談,縱觀東晉六朝和南宋,都先後有強勢人物站出來,如桓溫,謝安,劉裕,嶽飛等人,他們不是自身有著強大的統治力就是有著後方朝廷的全力支持,所以不僅能劃江而治,還能北伐中原。但是南明自南京被破就成瞭一盤散沙,雖然有晉王李定國這樣的人物,也沒辦法團結所有人支持他,鄭成功就經常不鳥李定國,內部不團結,沒有強有力的向心力,談什麼劃江而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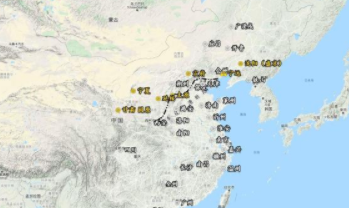
王朝陌路,積重難返,天下大事,無人可為。
萬歷十四年開始以申時行為首的百官就請求萬歷早定國本,薑應麟,沈璟上疏進諫被貶,這明明是整個官僚體系都認可立長的事,怎麼就成瞭東林黨一傢的要求瞭?那個時候離顧憲成萬歷三十八年下野回傢辦東林書院還有24年,合著爭國本都特麼怪東林黨唄?還有,利用京察排除異己的還真特麼不是東林,是沈一貫為首的浙黨,萬歷三十三年沈一貫京察中庇護私人錢夢皋,鐘兆鬥等人,逼走瞭時稱名臣的溫純,為瞭不讓楊時喬主持京察刻意貶低他,推薦自己的人蕭大亨主持京察。東林其實氣節不差,文官的總督巡撫大多殉國,東林的孫承宗全傢殉國,沒人提罷瞭,一個水太冷,天天說。相反,明末,投降的大多數是監軍和總兵。擁兵自重的將軍們,從關寧到江北四鎮,就沒幾個忠臣……到最後,南明依靠的軍事力量全是李闖和張獻忠的殘餘力量,沒幾個真正的明軍……真正對不起國傢的,就是這些吸血全國的軍閥,絕非東林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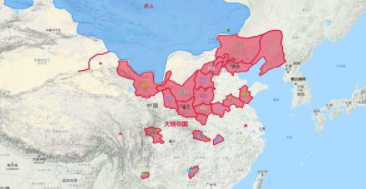
東林黨立新帝確有私心,但是迎立新帝也不是東林黨一個人說瞭算的,史可法自己也舉棋不定,直到馬士英也私下與史可法相商,肯定的說立潞王,史可法才下定決心寫瞭福王“七不可立”的理由。結果馬士英轉頭就把史可法和東林黨賣瞭,和四鎮聯合,自己獨取迎立之功。這個禍根可以說東林也是被坑的一方,要是知道誰是皇帝東林還有必要去觸那個黴頭?所以說什麼都怪到東林身上是不對的,任何事情發生都是多種因素促成的。
西北大災,魏忠賢免去西北賦稅,關鍵時刻雪中送炭,穩定瞭西北民心,崇禎上臺以後西北征稅,取消驛站,李自成因失業、賦稅過重造反,請問這些說法屬實嗎?隻說一句,舊餉是按照萬歷十年的《會計錄》來征收的,可能細節有變動,但大體是不變的。遼餉則是除瞭貴州及直隸一部分地方外,每畝都加九厘,直到崇禎三年十二月,才由九厘加到一分二厘,這時候李自成起義都多久瞭?另外,明末農民起義的起點就是天啟七年三月,鄭彥夫等殺陜西澄城知縣張鬥耀,原因就是張鬥耀催科急。之後閹黨戶部尚書郭允厚上疏辭職,還專門提到瞭陜西因為催科嚴重,知縣被民變群眾殺死這件事。
崇禎元年五月初九上召諸臣於平臺,諭輔臣來宗道等曰:票擬之事,須悉心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重,會推宜慎。責戶部帑金零星,邊餉措辦無術,侍郎王傢楨引罪,遂論及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語良久,上未悉,命內使授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一切用法務先平允,已出故給事中毛士龍辨疏,問果枉否?諸臣俱曰:士龍事屬風影,望皇上寬之,各頓首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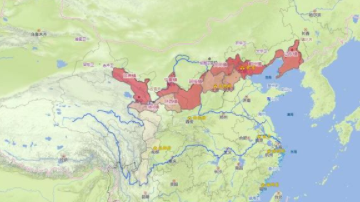
孫承宗作為東林全傢殉國你又可曾知道?問題是就算錢謙益,頂多是沒有死,對國傢危害並不大,放進滿清的是吳三桂,給滿清做馬前卒的也是各路總兵們。軍人逗投降瞭,甚至圍剿南明比滿洲還狠毒,你們卻苛求一個文人,說你怎麼不去死,簡直就是笑話。馮銓、孫之獬還有燕齊的一大堆士大夫當然是閹黨,他們因為在明朝喪失瞭政治生命而轉投大清國,這沒有什麼問題。然而阮大鋮就是東林黨人啊,他是左光鬥的同鄉,被東林黨人推入六科。但是東林黨內主流派要讓更加嫡系的魏大中取代他,他一怒之下退出東林勢力。但也沒有直接投靠閹黨,而是回瞭老傢。崇禎初期閹黨垮臺後,他東山再起,窺伺風向,上兩道奏章,一道專攻魏忠賢而另一道同時排斥所有的黨派,結果替他傳話的人為瞭自己的政治利益獻瞭第二道,從此阮大鋮被打成閹黨。但是阮大鋮還在給東林辦事啊,籌款給東林巨子周延儒當復相的政治獻金,結果呢?被一幫復社後生趕出南都。阮大鋮分明就是被東林黨內一些人“打成閹黨”的政治冤案受害者好不好,所以後來才要反東林。
馬士英更是東林黨人瞭。他是復社巨子張溥的好友,張溥因為幫助周延儒行賄而死於東林內部傾軋之後,是他給張溥收的屍。南都時期僅僅因為他是執政,又幫阮大鋮取得瞭一個職位,就遭到東林人士瘋狂進攻,甚至到瞭制造政治謠言、陰謀顛覆弘光(童妃案)、興兵大打內戰(左良玉東下)的地步。如果說氣節,太監們的氣節未必更好,別拿王承恩殉國個例說事,那孫承宗全傢殉國,無一投降呢?也沒見誰說東林有氣節啊,一個水太冷天天說……如果說治國失誤,這個鍋也不是東林背,文人不交稅,這個是朱八八的政策,東林頂多是沒有革自己的命而已,但人都是趨利避害,有幾個能革自己的命?明朝失敗的原因主要是國傢財政崩潰,國傢動員力下降到零,再深層的原因是制度僵化,朱元璋那一套根本不合時宜瞭,卻無法改變。

崇禎三年正月十六,戶部尚書畢自嚴上瞭一篇《條議理財足用六款疏》,疏內明確提到遼餉田畝加派九厘,仍然入不敷出,需要在於九厘之外,增派三厘,北直六府則每畝加派九厘,總計增派的田畝可得銀1439000餘兩,朱由檢批復【這條議六款,著該部還同該科參酌長便,並有未盡事宜一並商確具奏。】
阮、馬的遭遇,恰恰反映出明朝的黨爭已經不可控制,到瞭內部養蠱的地步。東林黨在外沒有瞭對手,就連自己人也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為此不惜發動內戰,讓天下淪入大清國之手。這些事夏允彝父子看得一清二楚,可笑黃宗羲卻還在山裡發明什麼弘光不是福王兒子的穢史。平心而論,北都之亡,過在崇禎,不在東林,由崇禎一意孤行而滅亡;南都之覆,過在東林,與弘光無涉。
第一:像我們一樣的老百姓合起來確實代表很強的底層力量,但其實人民的眼睛並不總是雪亮的。
第二:魏忠賢實際代表的是皇權 東林黨代表的是地主官僚集團 這兩者雖然都是統治集團,但在面臨亡國之險時誰更關心國傢 這個早有定論第三:氣節是個很扯淡的玩意,能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晚明需要能挽回局勢的能人而不是平時高談闊論,對時局無絲毫辦法,最後隻落個殺生成人的所謂君子 於謙要不是由挽狂瀾於既倒的神通,隻憑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間是無法名垂千古的第四:魯迅先生的史評可以參考,但你拿來當真理給這個討論下定論就太過分瞭

直到崇禎三年八月,兵部尚書梁廷棟上《題為恭敬九邊圖考,乞敕發戶部與臣部悉心講求,以復祖宗舊章》疏,提出【今日邊餉之不足,確由於錢糧不完,錢糧不完,確由於民窮,而民窮之故,全在官貪。故使貪風不除,不但加派民不能堪,即不加派,民之窮苦猶故也。貪風一止,不但不必加派,即再加派數厘,民之懽悅猶然也。】,於是崇禎批復【兵餉相需,全在幹濟得人,清厘有法,否則漏卮難塞。至謂民窮之源由於官貪,尤切中時弊,以後外吏誅求,責成撫按,在內餽遺,責在廵城,如有違犯及容隱者,並寘重典。其加派等事,即同戶部從詳確議以聞。】再一次將田畝加派擺到臺面上。
東林黨為瞭把熊廷弼救出來搭進去多少人啊,周朝瑞,袁化中都因為被污蔑收瞭熊廷弼的賄賂被活活打死在詔獄,最後熊廷弼被平反,首級能被帶回傢安葬也多虧韓爌等人帶頭上書。熊廷弼和東林黨關系密切可見一斑,甚至李棪先生的《東林黨籍考》直接把熊廷弼當東林黨人列入其中,居然還睜著眼睛說瞎話熊廷弼是閹黨?真是可笑至極。孫之獬妄人一個,可能是某種現在我們已經不知道的偏狹意識形態的狂信徒,在這裡不做討論。
馮銓呢?在洪太時期,他可是堪稱“自帶幹糧抗清”的“名將”瞭。楊漣的好友、東林黨人梅之渙稱贊他:“節次以來,涿鹿獨獲安堵,伊誰力耶?深山窮谷猶盡知之。”可他在明朝的下場如何呢?
清廷一來,便以為首席大學士,位在攝政王頭號親信文臣、滿洲人剛林之上。你覺得大清國該不該得河北士大夫之心?
崇禎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由檢正式下詔【向緣東事倥傯,履畝增賦,豁寢無日,久軫朕懷。乃邇來邊患靡寧,軍興益急,戶部諮奏再三,請於每畝除見加九厘外,仍再徵銀三厘,前後共銀一分二厘,惟北直保河六府向議免徵,今量行每畝加徵六厘,前項俱作遼餉,事平即行停止。朕因廷議既協,權宜允從,凡我百姓,各有同仇之志,能無好義之思?其有則壤不等,法須變通者,或照糧數議增,但期無失本額,又或委係災疲,且經兵擾勢難加賦者,撫、按據實奏明,取旨裁奪。】
1、其實直到天啟六年二月十一日戶部尚書李起元還在上書說自己提出的各項的建議,讓省直各地實行,但卻沒有一個回復的,清皇上下旨要求各省直於4月份回奏。
2、事實上,早在天啟六年二月十七,崔呈秀就上書指責復榷稅導致“出途疊征”是惡政。為此提出恢復榷稅建議的李起元還專門向皇帝上過揭帖解釋。
3、福建之所以收到瞭4000兩,是因為早在戶部李起元尚未提議恢復榷稅之前的天啟五年八月,福建地方官員為瞭籌措對付荷蘭人的軍餉,希望恢復閩安、竹崎等十二處關稅來湊軍餉。額征2萬3千4百。戶部討論後福建一半留著當兵餉,一半送到戶部濟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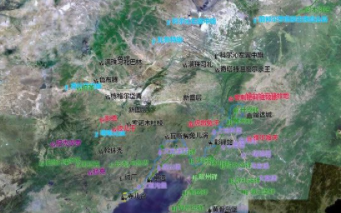
天啟元年汪應蛟說:"臣惟遼左用兵三載於茲,自遼沈繼陷,時勢益危,前議兵止十七八萬,今三路佈置共二十六萬,並薊遼總督添募將三十萬矣。前議餉止八百萬,今增至一千二百萬,或雲當千五百萬矣".看到瞭嗎?上千萬兩的遼事經費?我突然想起瞭當年宋太祖存錢準備買遼人人頭的故事,有這錢,花錢一百兩買一個女真人頭,一千萬兩白銀都可以幹掉十萬女真男子瞭....按這種預算,這大明朝是不用活瞭,如果沒有內帑支撐,根本玩不轉,一開始運作,錢怎麼算都是不夠的(且不說這錢花的是否合理),然後不夠的情況下隻能專供遼鎮,那麼別的邊鎮就隻能拖欠瞭,然後就算全給瞭遼鎮也不夠啊,那就是不斷地割肉養後金.........
按這幫牛人策劃,三大役怎可能才花一千萬........至少要一億兩白銀吧,畢竟天南地北,三個大方向呢。所以,隻要按當時議定的方案玩,遲早是玩蛋的,我也不知道魏大管傢是怎麼處理這問題的,按理來說,拖欠是解決不瞭的問題,魏老大若還玩拖欠,那各邊不早造反光瞭?闖王不用等到崇禎朝瞭。所以,要麼開源頭,要麼節流,要麼兩手一起動,否則不可能不出事的,他隻是個太監,不是聖鬥士。魏忠賢歷書上說其貪污比比皆是,嗯,還說回傢是帶瞭無數傢財,結果案發後處理。張居正傢還抄瞭近二十萬兩銀子(那土地之說可以省瞭),嚴嵩一傢子加在一起倒是有個兩百來萬銀子。魏倒是歷代少有的,世人皆稱其貪,卻沒有實據。若魏真撈瞭很多錢,朝庭都那樣瞭,他要麼貪軍費,要麼就是搞灰色收入(與民爭利),否則基本沒啥別的來源(什麼,還有買官?這個....),若是要大膽猜一下,莫非這傢夥學雷鋒,把錢存內帑裡花掉?
李明睿議南遷(正月初三日),上召左中允李明睿陛見。明睿,南昌人,以總憲李邦華、總督呂大器特薦,起田間。至是召對德正殿。上問禦寇之策,明睿請屏左右密陳,趨進禦案。言臣自蒙召以來,探聽賊信頗惡,今且近逼畿甸,此誠危急存亡之秋,隻有南遷一策,可緩目前之急。上曰:此事重,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言上天未知如何。明睿曰:天命微密,當內斷聖心,勿致噬臍之憂。上四顧無人雲: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但外邊不從奈何。此事重大,爾宜密之,切不可輕泄。泄則罪將坐汝。上還宮,賜宴文昭閣。及太原陷,明睿復疏勸,上深許之。下部速議,而兵科給事中光時亨首參為邪說,言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上曰:光時亨阻朕南行,本應處斬,姑饒這遭。然而南遷之議寢矣。
士紳優免、投寄、詭寄等的問題。再優秀、再忠誠的那些文臣,他們都沒有主動交稅的,沒有主動放棄優免待遇的,最多比較克制一點而已。左光鬥沒有放棄,汪應蛟沒有,史可法盧向升楊漣孫傳庭統統沒有。明末財政崩潰並非因為商稅收不上來,而是因為農稅收不上來。那時候商業沒那麼大用。銀子再多又如何?當吃還是當穿?農稅收不上來,一方面農民負擔無法承受最終守著土地餓死或放棄土地成為流民。一方面在冊交稅的人越來越少。至於為黨爭不顧國事的事情,明朝人自己的筆記也沒少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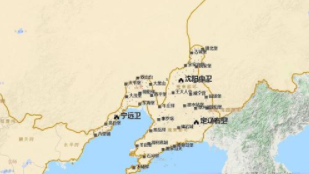
否則李自成何置於區區幾年就打進北京?因為朝廷已經徹底在臣民中失去信任。要不是後來有異族入侵,明朝的形象會遠比現在糟糕。雪崩之時,沒有一片雪花無辜。閹黨這片雪花固然罪該萬死,東林這片雪花也大哥別說二哥。你們是當權者,國傢忘瞭,你們不負責誰負責?難道是那些沒有權利的被壓榨百姓嗎?文人不交稅又不是東林發明的?就算在明朝也是朱八八的政策,有句現代的話,好制度使鬼變成人,壞制度剛好相反,人都是趨利避害的,這個怎麼能苛責?壞就壞在定下這種制度又無任何改良機制。至於東林的氣節,總體上比太監們強多瞭。至於危害,明末危害最大的是各路軍閥,從關寧到江北四鎮,幾乎沒一個好東西,這個鍋也扣不到東林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