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地位怎麼樣?天津的地位是怎麼迅速上升的?
今天小編為大傢帶來天津的地位是怎麼迅速上升的?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天津這個城市在同治九年(1870)以前,地位並不重要,按照行政劃分來說屬於“道”這個級別,也就是地級市。剛剛接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也認為省會保定是“控扼”直隸的中心,而天津則“偏在一隅,似非督臣久駐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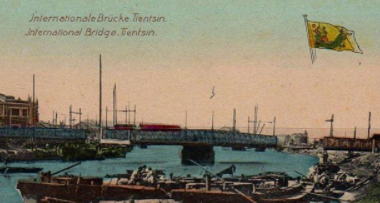
天津的地位是如何發生轉變並最終升格為總督駐地的呢?這與震驚全世界的”天津教案“有關,這說來就話長瞭。
此前的天津在官員設置上比較復雜,理論上最高的長官是“三口通商大臣”,但他又不是地方行政長官,而是隸屬於總理衙門,隻負責外交與通商,並不能過問民政;民政則由地方官天津道、府、縣三級管理。由於三口通商大臣是中央級別的,而天津道等級別過低無法提供相應的行政資源支持。所以形成瞭無法匹配、難以協調的局面。
天津教案發生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受命出使法國“謝罪”,總理衙門派出大臣毛昶熙代理三口通商大臣。毛昶熙具體參與瞭教案善後的主要談判,深切體會到瞭天津在機構設置上的尷尬,因而他上疏建議裁撤專職的通商大臣,由直隸總督兼任。

清廷采納瞭這個建議,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改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隸總督兼任。這一舉措,也讓天津的地位得到瞭相應的改變,自李鴻章接任第一任北洋大臣之後,其駐地就以天津為主,每年隻在天津封凍之後返回保定。而且,如果天津無法脫身,可以不必回保定。
這個時候,李鴻章本人對於天津的看法也發生瞭相應的轉變,他提出:“天下大勢,首重畿輔。中原有事,則患在河防;中原無事,則患在海防。”也就是說,保定與天津之間,究竟哪個城市適合作為直隸的中心,關鍵要看中原是否有事。中原有事,直隸的河防就是拱衛京師的關鍵。

不過以當時的形勢來看,太平天國和捻軍均被剿滅,中原顯然無大事。而天津由於通商開埠,公使駐京,成為瞭往來要沖。因此,李鴻章個人雖然留戀保定,卻也認為應該抬高天津的城市定位。
自此,直隸便有瞭兩個中心城市。除瞭總督衙門改駐天津外,別的機關一律留駐保定,有佈政使負責日常事務,重大事件請示總督裁定。從清代各種文件來看,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依然將保定看成是直隸的省城。至於天津,當然也不再是“偏在一隅”的小城,而成瞭影響力超過省城的城市。
李鴻章駐天津後,馬上就發現瞭一個棘手的問題。他以封疆大吏兼任北洋大臣,而面對的往往是一些無關緊要的通商事務,甚至還時不時地與小小的領事平行照會,這不免有損國體,對李鴻章個人來說,臉面上也過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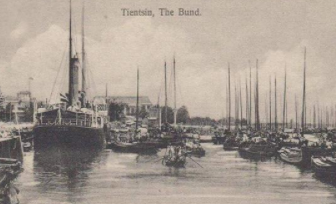
因而,天津海關道便應運而生瞭。李鴻章上任不久,便奏請設立天津海關道,由原來的天津道兼任。以級別而言,海關道與各國領事平級,雙方交往使用平行文書。更深一步,從實際工作效率來看,直隸總督本就是疆臣之首,日理萬機,如今又兼任北洋大臣,如果與外國領事們平級相處,則必然將大量涉外事務吸引到自己手上,限於瑣事之中。
天津海關道的設立,不僅確保專人負責繁重而微妙的外交通商工作,而且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乃至清廷在外交事務中獲得極大的緩沖餘地。同時,專職的天津海關道也有利於理順關稅征收體制,日後的歷史證明,這個職位果然成為李鴻章的理財工具,與天津海關稅務司一起,對千瘡百孔的直隸財政乃至中央財政貢獻頗大,也保證瞭李鴻章各項改革措施的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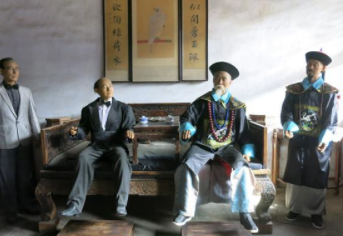
可以看出,天津的歷史地位是因“天津教案”後發生改變的,更確切地說,是由於李鴻章兼任北洋大臣而一手打造的。自此以後,天津在全國的地位迅速上升,成瞭僅次於北京的戰略要地。
